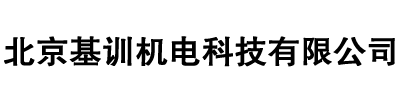7年NBA生涯被裁7次,空有滿格天賦,卻始終無法立足!或重返CBA
近日,前上海男籃的外援諾阿-馮萊被爆料有望加盟遼寧男籃,對此,諾阿-馮萊在社交媒體上給出了回應,確實和他們有過商討,他們很想得到我,但是我還得考慮一下未來的規劃。換而言之,遼籃很想得到諾阿-馮萊,但是后者顯然還想沖擊一下NBA。回望他的籃球路:24.8厘米長、29.8厘米寬的巨掌(曾是NBA新秀體測第二大),NCAA賽場48.5%的三分命中率,高中時期場均17分12籃板的統治力,無一不證明他擁有“兌現巨星潛力”的資本。可現實卻是——7年NBA生涯,輾轉7支球隊,7次面臨裁員或被交易的命運,最終在26歲那年被聯盟拋棄。這個流淌著利比里亞貴族血液的“球癡”,為何始終無法在NBA兌現一身天賦?

一、傷病:撕碎新秀賽季的“成長期門票”
對NBA新秀而言,生涯前兩個賽季是“扎根聯盟”的關鍵窗口——適應節奏、建立自信、找到角色定位,每一步都不可或缺。而馮萊的NBA之旅,從起點就被傷病按下了“暫停鍵”。2014年選秀夜,夏洛特黃蜂(現鵜鶘)以第9順位選中馮萊時,球探報告上寫滿了期待:“2.08米身高+2.24米臂展,能投三分的內線,完美適配小球時代”,甚至將他與剛拿到兩冠的克里斯-波什對比。可就在他準備開啟新秀賽季時,運動型疝氣手術突然襲來——這一傷病不僅讓他缺席了訓練營和季前賽,更直接導致他新秀賽季僅出戰25場,場均僅得3.3分3.4籃板,投籃命中率不足40%。
彼時的NBA,同屆新秀正飛速成長:安德魯-維金斯場均16.9分當選最佳新秀,喬爾-恩比德雖也受傷,但憑借天賦仍被視為費城未來核心,而馮萊則在病床與替補席的交替中,錯過了“適應NBA強度”的最佳時機。更致命的是,這次傷病打亂了他的技術打磨節奏——大學時期他賴以生存的“三分+籃板”組合,在NBA的高強度對抗下本需時間調整,可傷病讓他失去了在比賽中試錯、改進的機會,等到傷愈回歸,黃蜂的戰術體系已沒有他的位置。當一名新秀在最該“漲球”的階段被迫停滯,后續的追趕便會格外艱難。馮萊的NBA生涯,從一開始就輸在了“起跑線上”。

二、定位:小球時代的“不三不四”困局
馮萊的天賦特點,本應是為“小球時代”量身打造的——能投三分、能搶籃板、還能運球過前場(利拉德曾評價“他能搶籃板同時運球過前場”)。可諷刺的是,正是“全能”的標簽,讓他陷入了NBA的“定位陷阱”。
在NBA的戰術體系里,內線球員通常被清晰地分為“五號位(純中鋒)”和“四號位(大前鋒)”,側翼則是“三號位(小前鋒)”。馮萊2.08米的身高,打五號位時對抗不足(面對傳統中鋒容易被壓制),打四號位時橫移速度又不如純側翼,打三號位時持球能力尚未達到明星級別——這種“不三不四”的特質,讓他成了每支球隊的“邊緣選項”。
在波特蘭開拓者時期,他曾單場抓下19籃板,展現出頂級的籃板嗅覺;在紐約尼克斯時,他場均能貢獻8.4分7.8籃板,三分命中率回升到34.1%,看似找到了節奏。可每當球隊需要“明確角色”時,馮萊總是第一個被犧牲的——開拓者需要能護框的純中鋒,尼克斯需要能穩定得分的側翼,沒人愿意為他設計“靈活站位”的戰術,更沒人給他足夠的時間去打磨“全能”的細節。
反觀他在CBA的成功,恰恰印證了這一困局的根源:上海男籃教練組沒有將他框在“四號位”或“五號位”的標簽里,而是讓他自由發揮——既能站外線投三分,也能沖內線搶籃板,還能在快攻中持球推進。當他在對陣北控的比賽中完成“搶斷+運球貫穿全場+大風車灌籃”時,那種“無所束縛”的狀態,正是他在NBA從未擁有過的。NBA的“精準定位”要求,反而扼殺了他的“全能天賦”。

三、漂泊:7年7隊,從未有過“穩定的土壤”
“如果一個球員連下賽季為哪支球隊效力都不知道,他怎么可能安心打磨技術?”這是馮萊在2021年離開NBA時,私下對朋友說的一句話。7年NBA生涯,他先后效力黃蜂、開拓者、公牛、尼克斯、森林狼、掘金、籃網7支球隊,平均每支球隊待不滿1年,這種“漂泊感”成了他兌現天賦的又一枷鎖。
每到一支新球隊,馮萊都要重新適應:適應新教練的戰術體系、適應新隊友的配合習慣、適應新的角色定位。在黃蜂,他是“需要證明自己的新秀”;在開拓者,他是“替補席的籃板補充”;在尼克斯,他是“臨時救火的內線”;在籃網,他甚至連穩定的出場時間都沒有。沒有球隊愿意將他視為“長期核心”,自然也不會為他投入資源——沒有專屬的訓練計劃,沒有戰術地位的傾斜,更沒有心理層面的疏導。

最典型的例子是2019-2020賽季:他先被森林狼交易到掘金,僅打了14場就被裁,隨后加盟籃網,卻在賽季結束后再次面臨裁員。短短一個賽季,他換了3支球隊,始終在“找狀態”和“被放棄”之間循環。當一名球員長期處于“隨時可能被裁”的焦慮中,他很難在比賽中展現出“統治級”的自信——投籃時會猶豫,防守時會畏縮,生怕一次失誤就失去出場機會。
對比他在上海男籃的經歷:球隊不僅給了他長期合同,還將他視為“防守核心”,即使他受傷,教練組也耐心等待他康復。這種“穩定感”讓他重新找回了對籃球的熱愛,馮萊最近一次在CBA效力是在2023-24賽季,14場常規賽,場均出場不足20分鐘,能得到11.6分5.9籃板1.8助攻0.7搶斷0.7蓋帽,經典一戰,是對陣吉林的比賽中狂攬24+20(籃板),成為上海隊史第8位雙20先生時,在CBA他的天賦得以釋放。遺憾的是,NBA的“流浪生涯”,從未給過他這樣的“成長土壤”。

心理:貴族血統的壓力與現實的落差
馮萊的成長環境,比大多數NBA球員更特殊——他流淌著利比里亞部落貴族的血液,家族客廳里掛著曾祖父布拉蘇在總統就職典禮上接受冊封的照片,家族會議室的墻上寫著“馮萊之名,重于泰山”。這種“家族榮譽”的壓力,從他接觸籃球的那天起就伴隨著他。
父親薩繆爾的教育理念是“做錯事會讓整個家族蒙羞”,這讓馮萊從小就養成了“嚴格要求自己”的習慣。十二歲第一次摸籃球時,他就因為“怕打不好丟家族的臉”而拼命訓練;十四歲在迪士尼堅持找球館,也是因為“不想浪費任何提升自己的時間”。這種執著曾讓他在高中和NCAA脫穎而出,但到了NBA,卻成了“心理負擔”。
每當他在NBA賽場上表現不佳時,他想到的不僅是“自己會被裁”,還有“會讓家族失望”。這種雙重壓力讓他在比賽中過于緊繃——投丟一個三分就會自責很久,搶不到一個籃板就會懷疑自己,反而無法發揮出正常水平。而在CBA,他遠離了“家族榮譽”的直接壓力,也遠離了“NBA球星”的光環,母親雷內爾在觀眾席上揮舞的利比里亞國旗,更多的是“支持”而非“期待”。當他在CBA賽場上露出久違的笑容時,那種“為自己而戰”的輕松感,正是他在NBA缺失的。

當馮萊在福建晉江的賽場上,看著父母揮舞的利比里亞國旗時,他或許終于明白:籃球的意義,從來不是“兌現天賦”的標簽,而是“找到熱愛”的初心。7年NBA生涯的漂泊與挫折,不是因為他“沒有天賦”,而是因為他的天賦,需要一片“不被定義、不被催促、不被施壓”的土壤。
在上海男籃的訓練館里,月光灑在他修長的身影上,那身影里既有曾祖父冊封時的莊嚴,也有母親打兩份工時的堅韌,更有十四歲少年在迪士尼尋找球館的執著。他或許永遠無法成為NBA的“克里斯-波什”,但他在CBA找回了“諾阿-馮萊”——那個純粹為籃球而戰的少年。對馮萊而言,重回NBA難度不小,而加盟遼籃則會讓他的職業生涯再度煥發青春。